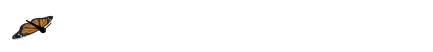
《方向》纸刊选稿平台
刘金山,笔名今珊、傲凌。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、《杂文选刊》特约撰稿人。在《河北文学》、《芒种》、《当代人》等刊物公开发表小说、散文三十余篇; 出版《草原依旧》、《百态凝思》、《世事人间》等三部文集; 短篇小说《十元汇款单》获河北"五个一工程"奖,散文《草原忆旧》获"世纪之光"二等奖。


1
老哥俩 / 刘金山
家住村东头的李来群和村西头的张有福要好了一辈子,是打从小玩尿泥巴长大的好哥们。这哥俩好像是对方肚子里的蛔虫,都很熟悉对方的脾气秉性和喜好,甚至都知道谁的身上哪个地儿长着颗痣,痣上长着几根毛。
李来群和张有福同岁,只是生月比他大一点。按辈份李来群管着这生月小的张有福叫三叔。“乡亲辈瞎胡论”他俩打小就觉得这么称呼很别扭。有一天,他俩就硬是把这瞎胡论的辈份给改了。张有福管着李来群叫大哥,李来群管着这张有福叫三弟,这么一叫就叫到了如今的头发白。
这李来群的命福不太好,因为他爹早年给山西军阀阎锡山当过几天兵,就为这,自打他记事起,头就从来没有抬起来过。都三十多岁了,才用自己的亲妹子换了个哑巴做媳妇。几年后,哑巴给他李来群生了个闺女。闺女很聪明,也考上了大学,毕业后在城里某个公司里做财会,也结了婚,生活过得很如意。就属李来群的哑巴老婆没福气,在生下闺女的第二年就病死了。李来群是又当爹来又当娘,一把屎一把尿的把闺女培养成了个名牌大学生。闺女成家后,多次要接他去到城里享清福,可他硬是不习惯住楼房,就是接受不了到处都是生面孔。住不了几天,就准的闹着回老家。老家凉屋子冷炕,整天价搂着个枕头过日子,但是他李来群觉得这样很舒坦。其实,他是舍不了村里的老哥们和祖宗留下的老宅子,也舍不得自己亲手翻盖起来的那几间破房子。
比起李来群,张有福的两个儿子从小就对念书不感冒,所以,考大学这条路没走成。但是,两个儿子在村里算是还本份,小日子也都还算是过得去。张有福的老伴直言快嘴,人送了个雅号“机关枪”。令张有福最得意的是老伴比自己小几岁,身子骨儿比自己还硬朗。他每天二两酒,每顿三个菜,小日子过得很滋润。
两个儿子成家后,张有福和老伴就开始单独起锅灶。张有福自幼脑袋瓜子灵。有生产队的时候就曾偷偷摸摸的做点小买卖,为此没少被罚工分挨批斗。生产队抄摊子以后,张有福第一时间就拆掉了自家的旧门楼,沿街盖起了个小卖部。
小卖部面积不大,很简陋,一溜用旧砖垒起的柜台,靠墙立戳着几个用旧木板搭成的货架子。货架子上摆放着油盐酱醋针头线脑,都是些个老百姓的日用生活品,数量都不大,样数还真不少。
自打张有福小卖部开张那日起,这李来群就想当然地成了小卖部的常客,每天必到,准时按点。每天一大早,总是李来群第一个敲开小卖部的门。其实这个时候,小卖部的柜台上早就摆放上了一壶酽茶,一针线笸箩旱叶子烟,一个脏兮兮的象棋盘,棋盘上散乱着些个木疙瘩。老哥俩先是抽着烟喝着茶塔东塔西的瞎侃胡聊,一会儿以后,就开始趴在柜台上下象棋,天天如此,日日如斯。
都很晚了,张有福还在电灯底下捏衔着一摞子散钱瞎倒腾。他一边数钱一边直摇头,连数了好几遍总也对不上荐口。“嘿!真他娘的怪事,钱怎么就差了呢?”张有福的脑袋摇的像个不楞鼓。“我说你老东西今儿个犯神经了你?你还让别人睡觉不”?老伴欠起身来冲他不爱烦地吼起来。“你他娘的别烦我成不?丢钱了,能睡得着吗?睡你姥姥个缵儿!”张有福没好气大声喊。
听说少了钱,张有福的老伴急忙坐起来帮着他对磨茬口,其实张有福对全天发生的每个细小的茬骨眼都已经想了好多遍。
“莫非…莫非…”老伴的心里有团疑云。
“什么莫非莫非的,我告你说,你可不要瞎鸡巴的猜乎行不?啊?”没等老伴说完张有福就急了白脸的抢白了她一句。“关灯,睡觉!有话明天再说”。张有福将头扎进了被子里,老伴也不再说什么。
第二天,天刚放亮。
“嗨!我说三弟昨儿个你咋的了?走的那几步臭棋,味儿可真够熏人的嗨!快摆上!今儿大哥再和你过两招”。李来群人还没跨进门槛,大嗓门早就惊动了张来福家的两口子。
“大哥,我看今儿是不是就别…别…”张有福磕巴的应答着,他张有福哪还有杀棋的精气神。
“你看,你又胆怯了不是?赖汉子没有三天的累怕,慢慢地来,会有长进的——”李来群故意把“长进”二字的发音拖长腔,嘴里哼哼着小曲儿,熟练地从柜台底下拽出了破棋盘,利索地摆放在了柜台上。
“我说大哥,你看今儿就…”张有福直想尽快地抖落出那块心病来。
“红先黑后输了不臭,你先走。”李来群哪知道他张来福这个时候有苦衷,早就摆出了肯定要赢的架势来。
张有福心里装着麻烦事,哪还有心思陪他打哈哈,跳马, 踩车,打闷攻,三下五除二就被杀得没路可走了。
“大哥我…我问你,你说咱…咱哥俩的交情怎么样?”张有福一边重新摆棋一边说,他还真不知怎么开这个口。
“这还用问吗?全村的老少爷们谁不知道咱哥俩就差没从一个娘肠子里爬出来!那叫亲呀!亲哥俩呀!”李来群一边重新摆放着棋子一边随口应答着。
“我说…我是说…”张有福还真个开不了这个口。
“说什么呀说,走棋,走棋。”李来群的两眼死盯在了棋盘上。
“大哥你…你…你还没弄…弄明白我的意思呢!”急得张有福真个的是跺脚捶胸打地转。
“你不就是想缴枪认输吗?嘿嘿!你大哥今儿个就是吃硬不吃软,缴枪?缴枪也得杀!杀你个鸡犬不留!杀你个片甲不归!杀你个…哈哈哈!”李来群不知从哪儿讨了点喜鹊屁吃,今儿他可真高兴。
“大哥,你听我…听我把…把话说完…说完行不?张有福的脖子根儿都憋红了。
“奶奶的!我说今儿个你怎的了?说话结结巴巴不成个句儿了!再看看你那熊鸡巴样,像憋着个蛋的老母鸡似的,要抱窝下崽呀你?真鸡巴操蛋!”李来群这时才把头抬起来,还真没见过张有福今天这个熊蛋样。
“大哥,那我说出来你可不要多心呀!”张有福把声音压得很低,先来了个投石问路。
“行!行!你就甭一个眼的叫驴瞎转磨了。”李来群显得有些不耐烦。
“大哥,你昨儿个刚进小铺时,我正在干什么你还记得不?”张有福说这话的时候用眼斜瞟了一下李来群。
“你不就是整天价鼓捣那几个臭钱吗?钱是什么东西?是身外之物!生不带来死不带去,真操鸡巴蛋!以后不要在我面前总是提钱钱的,我烦这个!知道不?”“那,我们在杀棋的时候,你就没看见有哪家的淘气小子钻进我那柜台里边去过?”李来群好像明白过来了,今儿个张来福还真的有话要说。他没有答言,只是不紧不慢地从屁股后面的裤腰带里抻出了那根旱烟袋,利索地把烟锅头塞进了旱烟荷包里面去。
咣当当……
放在小铺外面窗户台上的什么家什被人碰翻了,掉在了地上,还滚出了老远。这冷不丁的响动把屋里两个老汉着实地吓了一大跳。
“咱就把话挑明了说吧!昨儿个我家小铺少了钱了!要是一星半点的也就算了,一百二,少了一百二十块呀!这一百二十块钱对我们老俩来说也算是个大数目了。再说了,我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!也不是坑他崩你骗来的,那是我们老俩起早贪黑赚来的!那叫血汗钱知道不?待得好好的钱就少了,这不是怪事吗?这总得有个原由吧!”张有福的老伴“机关枪”撩门帘进来,脖子不是个脖子脸不是脸地冲着屋里就扫了这么一梭子。
“滚你娘的个蛋!你个臭老娘儿们家的瞎掺乎什么?还反了你!奶奶的!”张有福窜起来指着老伴的鼻子大声骂起来。
张有福的老伴瞥了一眼李来群,嘴里嘟囔着退出了门。
费了好大劲,李来群才从口袋里摸索出来了个打火机,卡嚓、卡嚓地连打了好多下,才点燃了烟锅里的旱叶子烟,随后,吧嗒!吧嗒!猛地吸了几大口。这叶子烟劲头大,呛得李来群好一阵地咳嗽。
“大哥,你可千万不要多心!我只是想让你帮着想想节骨眼!绝对没有别的意思,真没别的意思,大哥。”张有福急忙倒了一杯热水,双手递给了李来群。
过了好大的一阵子,李来群才慢慢地抬起头,坦然地望着张有福说:三弟,你们不提,我还真忘了这茬口了。怎么说呢?李来群抬脚磕打掉了旱烟锅子里的烟灰,又拧上了一锅,慢慢的点燃,深深的吸了一口接着说:是这样,我这两天手头儿确实有点儿紧巴,需要用点儿钱。正巧,我昨儿个看见你柜上放着一摞钱,就顺手抽了几张,本想过两天就给你补上,所以,也…也没,咳!你瞧我这个人,怎么昨个儿就没直接和你说清楚?看闹得你们着急上火的!这…这…看搞的这个…。李来群一口气喝干了杯里的水,继续说:不过这点请你俩放心,过两天我肯定会如数还给你们的。“大哥,甭说了,你就甭再说了行不?这钱只要是你拿了就好。话不说不清,事儿不谈不明嘛!再说了,不就是百十来块钱嘛!咱俩谁跟谁呀。你甭把它撂心上,如果今后再有困难需要钱的话,你就明大明地跟我直接说不就结了吗?咱哥俩这是谁跟谁?”张有福说这些话时没有半句打磕巴。
第二天,日头老高,张有福的小铺也早就开了门,可李来群却还没有来。
都三天了,李来群他还是没有露个面。
张有福已经挨过老伴好几次的挖苦数落了。张有福的心里总觉得有点不是个滋味。
第四天,张有福起得很晚,要不是门外那讨厌的敲门声,他真想来它个停止营业,睡它个呼呼连轴转。
“老爷儿都照着你的屁股啦,还没起呀!”是大哥的声音,张有福一骨碌滚下了炕,没来得及把胳膊完全伸到袖子里,就趿拉着鞋往外跑。
敲门的果然是他,李来群。
“大哥,你这两天跑哪去了,也不打个照面。我还以为咱俩的交情掰了呢?”张有福拉住了大哥的手,他的眼圈有些红润了,哽咽着地连声埋怨着说。
“哪能呢!哪能呢!我是到闺女那儿去了一趟,本想当天就赶回来,所以临走时也没跟你打招呼,可他们死乞白赖地非留我住两天。这不,刚回到家就找你报到来了不是?嘿,你瞧嗨!徐水刘伶醉、漕河小驴肉,槐茂酱菜外带高碑店的豆腐丝,今儿个咱哥俩痛痛快快地喝两杯!”李来群将手里提溜着的塑料兜抬得老高老高的。
“老东西,快摆弄几个菜,今天我要和大哥痛痛快快地喝两杯!”张有福撩起门帘朝着院子里大声的喊。
很长时间,张有福的老伴才撩门帘进来,先和李来群打了个不冷不热的招呼,尔后将两盘炒菜摆放在了柜台上,然后甩身走出去。李来群看得出来这老弟媳妇的心情不怎么好。
这刘伶醉有劲儿但是不辣喉,老哥俩喝得很过瘾!
“喂!我说你,你过来给大哥敬杯酒行不?真他奶奶的三八赶集四六不懂的玩意儿,纯粹他娘的一个短调教的东西!”张有福再次地扯着个破锣嗓子喊,这已经是他好几次招呼他的老伴了。
张有福患有老年性前列腺炎,这尿儿就是多,每次瞅老伴在屋当儿,他就准得往院子里的茅房跑。
张有福提溜着裤子,摇晃着身子,撞了门框好几下才算进得屋里来。李来群抹了一下眼屎,强睁着眼睛伸手指着张来福裤裆上的那湿乎乎的一片说:老弟,你那个…那个玩意可…可真他娘的…不…不争气,它…它在裤…裤裆里面就哭…哭啦?张有福接茬道:老了,这玩意也他奶奶的不听使唤了,不使劲抻它…它…它还真的懒怠出来!所以,就…就…哈哈哈!来喝…喝酒!喝它娘的个七七四十九…九杯酒!他俩都喝到火候了。
太阳偏西了。李来群晃荡着身子站起来,扶着墙走到了张有福的老伴面前说:弟妹,这是一百二十块…块钱,给你。当面点钱不算薄,你要点…点好,一百二十块,一分可…可都不…不少!李来群从衣袋里费劲地掏出来了个纸包包,重重地拍在了柜台上,扭身出门,踉踉跄跄地朝着村东头方向走去。
从春暖花开到暑去秋来,老哥俩还是像往常一样天天凑在一起看电视,杀象棋,谈天说地,胡侃瞎聊。其实他俩心里已经有了一堵墙。
又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,街上玩耍的小儿们又唱起了那古老的歌谣:小朋友不要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,腊八粥,喝几天,眼看就到二十三,二十三糖挂粘,二十四扫房日……
春节快要到了,家家都在置办年货,户户都在打扫房间。张有福趁两个小孙子放年假了不上学,图有个帮手,也要把小卖部的叽里旮旯好好地拾掇一下过大年。
“爷爷,快来呀!这里有钱!”两个小孙子惊奇地发现了从三屉桌与柜台的夹缝里钻出来的一地钱。
张有福猫腰拣起了散落在地上的已经沾满了灰土的钱,用舌头不时地舔一下拇指尖,老伴在一旁愣呆呆地瞅着他一张一张地在数钱。十块、二十、三十…正好一百二十块。
张有福像是一根木头,在李来群家门口立戳了老半天才敲门。
一见面,张有福就紧紧地攥住李来群的手,老半天没有说话只是在摇头,眼角淌出了老泪来。很久,他才从口袋里掏出那一百二十块钱,用他那双发颤的手递给了李来群。
“闺女!快鼓捣几个菜,把我那几瓶刘伶醉全都拿出来,今儿个我要和你三叔喝它个痛快!李来群招呼着闺女。闺女是来接他进城过年的。
春节很快地过去了,张有福老汉的小卖部也早已开张营业。
转眼又一个暑去冬来,张有福的小卖部与往常并没有什么两样,只是李来群一直还没有来过。

责任编辑:谢虹
微信ID:西后街三十二号

长按二维码关注我
总编:文夫
主编:谢虹
首席顾问:林莽、蓝野、 桫椤、张劲鹰、
石英杰、温经天、邢丽红
责任编辑:刘金山、蒲力刚、刘冬、
扈克勇、李长胜、林红芝、王勇、
徐银杰、李丹、梁雨薇
主管:《诗探索》保定联络站
协办:徐水作家协会、徐水新华书店
投稿邮箱:573836905@qq.com
主编微信:XsXiehong
出版周期:半年刊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