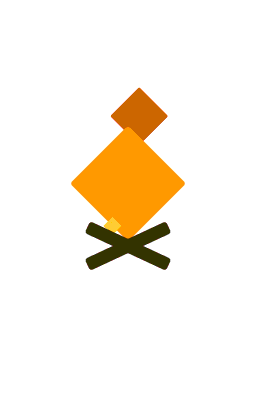一个人获得性高潮要多久?
短则几分钟,长则十几分钟。
如果他是残疾人呢?
可能几十年,可能一辈子也无法达到。
在被忌讳的性与爱面前,正常成了8500万残疾人求之不得的奢望。

残疾人不需要爱,更不需要性。
这是社会公开的秘密。
我小时候,小区住着一个同龄脑瘫女孩。
为了方便照顾,父母总把她的头发剪得极短。
到了青春期,甚至没有穿胸罩。
偶尔我看见妈妈推着她在小区散步。
坐在轮椅上,近乎光头,身体缩成一团。
只有宽松衣服下鼓起的胸部,透露出她也是个十几岁,也许和我一样爱美的女孩。

一个人失去一条腿,或者丧失一部分智力。
为了方便照料,他的成长通常被默认是「去性化」的。
不分男女,更没有七情六欲。
性教育的捉襟见肘,在残疾人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。
登上《奇葩说》的盲人蔡聪曾在长春特殊教育学院上学。
学到人体解剖学,要讲生殖系统那一章时,大家都很期待。
没想到,老师进来撂下一句话,这章自习。
蔡聪气愤地反驳,我们都成年了,为什么不讲?
老师没当回事,反正你们也用不着。

蔡聪
听起来是不是很像我们中学上生理卫生课,老师直接跳过的场景?
可是,那时蔡聪已经上大学,不是小孩子。
而且,他学的是针灸推拿,正儿八经的医学专业。
性教育对残疾人集体缺失。
当他们踏进社会,鼓起勇气表达性、触碰性,会遭遇更大的困境。
蔡聪后来就职于一家残障人公益机构。
有一次,他的盲人同事去情趣用品店买东西。
一进门,店主上下打量,开口就是一句:
你走错了吧?
言下之意就是:
你都这样了,还想那事呢?
生而为人,众生平等。
为什么残疾人就不能渴望性?
因为在大众眼中,你一旦残疾了,就和儿童没什么区别。
可以和儿童一样闹情绪,需要额外的照顾。
但你见过儿童要求性吗?
一旦残疾人与性联系,他们的身体缺陷被放大,成了大众眼光中的性猎奇。
在电影《绿洲》里,智障者洪忠都与脑瘫者韩恭洙相爱。
两人情到浓时,发生关系,忠都却被污蔑为性侵,还被警察讽刺:
你口味真够重的。
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,为何要去「强奸」一个全身抽搐且奇丑无比的女人?

《绿洲》
2019年了,我们已经敢于承认性的美好。
可是,在以「正常」自居的大众建立的社会规则里,残疾人的性爱依然会被贴上丑陋的标签。
他们需要关怀,需要照顾。
却唯独不需要性。

然而,一个人残疾了,对性爱的渴求就会随之消失吗?
不会。
他们甚至比普通人更渴望性与爱。
北京慧灵机构工作人员方玉翔,有一个智障女儿芳芳。
她喜欢的男孩叫张夏,是个脑瘫男孩。
为了靠近张夏,芳芳总是给他喂饭,推着他去散步。
张夏吃东西流口水,芳芳就拿手绢给他擦。
轻轻地,慢慢地擦,温柔得如同新婚妻子。
芳芳最大的愿望,就是能亲亲张夏。
方玉翔再三请求,张夏好不容易同意了这个要求。
说好只亲一下。
结果,芳芳很羞涩地抓住张夏,情不自禁地亲了三下。
性不是一个器官对一个器官的回应,而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靠近。
一般人如此,残疾人也不例外。
如果你读过2014年那首横空出世的诗——《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》,
你会被这种热烈打动。
我是穿过枪林弹雨去睡你,
我是无数个我奔跑成一个我去睡你。
这首诗的作者,是残疾诗人余秀华。
先天脑瘫导致她行动不便、口齿不清。
就连写字,也要一只手努力按住另一只发抖的手。
但她坐在家门口小板凳上,颤抖着写出的字句让所有人都震撼了:
我的身体全是声音,而雨没有到来。

没有避讳,没有遮掩,有的只是比一般人更直白,蓬勃的生命力。
即使大部分肢体丧失机能,内心对性的渴望也不会消失。
如同《亲密治疗》中的马克。
马克38岁了,他生活大部分时间的状态是,躺着,靠呼吸器维生。
打字、翻书和拨电话,全用嘴叼着木棍完成。

这副看上去脆弱得随时会折断的躯干,依然欲望汹涌。
向女护工求爱不成,他向神父喃喃祈祷:
上帝没有阻止我拥有性欲,只告诉我这性欲是多么没用。
像马克这样的残疾人还有多少?
有性学家曾对中风幸存男性进行调查。
他们虽然患不同程度的偏瘫、失语、站立不稳和行走不便,但仍有性欲者占84.1%。

压抑下,残疾人只能偷偷摸摸探索着性。 几乎所有男孩都在青春期尝试过自慰:深夜关上房门,打开小网站,在A片画面中获得性爱初体验。 残疾男孩的探索则艰难得多。有人高位截肢,性器官已经丧失感觉。有人连穿衣都成困难,更别提把手伸到私处。
即使是那些有能力自慰的男生,也比常人忐忑百倍。一听到有动静,他们要花比一般人多10倍的功夫,才能拉上那几厘米的裤链。 没有亲身体验的可能,就摸索其他一切办法。 蔡聪上盲校时,学校里聋盲混住。每当听障人把女朋友带回宿舍,墙那边传来一丝动静。隔壁的盲人同学就呼朋唤友:快快快,那边有节目!
然后蹑手蹑脚趴在墙根,集体竖起耳朵。
仿佛通过耳朵,就能「看」光墙那边的一举一动。 偷听看似「猥琐」,背后隐藏着视障人的无奈。一面是不能说的禁忌,一面是无法抑制的悸动。
北京一家盲人按摩院的王师傅告诉我,因为看不见,深夜看A片时,他只能凭借影片的声响,再加上白天接触到的女性身材和声音,在脑海里一边想象性爱的画面,一边躲在被子里偷偷自慰。

《推拿》
黑暗中,逼仄的按摩室摆了十几张窄窄的按摩床。在距离王师傅不到一米的另一张床上,同事正发出熟睡的齁声。 但伴随着巨大快感降临的,是更大的孤独和无力感。你发现了它,却不能享受它。 因暴力袭击失明的法国盲人作家于格,在自传《残杀光明》里写下这样一段话:他没有家庭,没有女人的温柔、孩子们的嬉笑和快乐。他用不着打开电灯,在黑暗里,启开一瓶罐头,吃完以后,躺下睡觉。为了给自己一点温柔,他在被子下面自慰。
性躲在暗处,残疾人也是。但于生活的暗处,在他们身边时刻发生的千百种美好的性,却很少能和这群人产生联系。

如果说残疾是上帝在人生中夺去一块,那不能体验性是又一块缺失。在这条路上,有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做出了努力。 在荷兰,部分地方政府为残疾人提供一个月三次性服务的费用。在澳大利亚,当地成立了一个专门为残疾人提供性服务的组织——感触之家。在这里,残障人士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性工作者上门服务。

无独有偶。台湾有一个叫手天使的团队。专门帮助重度障碍者和视力障碍者自慰,并且完全免费。

这个手势是手天使的标志 图源:一条
5年时间里,手天使服务了21个残疾人,每个耗时2到3个月。比起单纯的打飞机,他们更想让残疾人体验到关怀和温柔。
3个月时间里,他们会用至少1个月,派出同等残障的义工和申请者聊天。然后找适合残障人通行的旅馆、布置场地,最后才是性服务。 因为怕被母亲发现,手天使的第一位女性申请者把网购的情趣内衣寄到团队负责人Vincent家里。情趣内衣要入水洗,于是,Vincent小心翼翼,清洗了人生第一件女士内裤。

手天使出任务时带的工具 图源:一条
然而,即使是极尽关怀的探索,在不少人眼里依然和色情服务无异。打开知乎搜索手天使,质疑比比皆是:不收费就是天使,收费就是技师。这事本质上,不就是性服务?还有检察官批评:他们游走在法律边缘,我却没有任何一条法律可以抓他。
该怎么定义针对残疾人的性服务呢?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,对于残疾人来说,对抗残缺的生活远比对抗这些批评复杂得多。
当性福来敲门,对他们来说不仅是身体上的满足,还意味着打开人生另一种可能。如同手天使的负责人Vincent所说:我们的工作不只是打飞机,是用欲望启动他们的人生。
接受完手天使服务后,重度肢体障碍患者Steven几乎是呐喊着,在日记中记录下那天的经历。他说,我终于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人。他开始寻找恋人,和健全人谈了两次恋爱,还去尝试了跳伞和冲浪。趴在冲浪板上,顺着浪花起伏,他从未尝试过如此畅快的人生。 也许,对于一般人来说,性的作用没有那么大。但在残疾人的生活中注入性与爱,像是慢慢缝合上生命中缺失的一块。你身体每一个褶皱,每一寸不完美的地方,在这里都能被接纳和珍视。 如同2018年春天,杜蕾斯发布的一首诗:光洒进暖流,花开在枝上,春光正好,我把你种在我身体里,然后一起躲进时间的皱褶里。 我想,我们每个人,都有权利体验这样自然、美好的性与爱。
- The End -





残疾人也能享受美好性爱